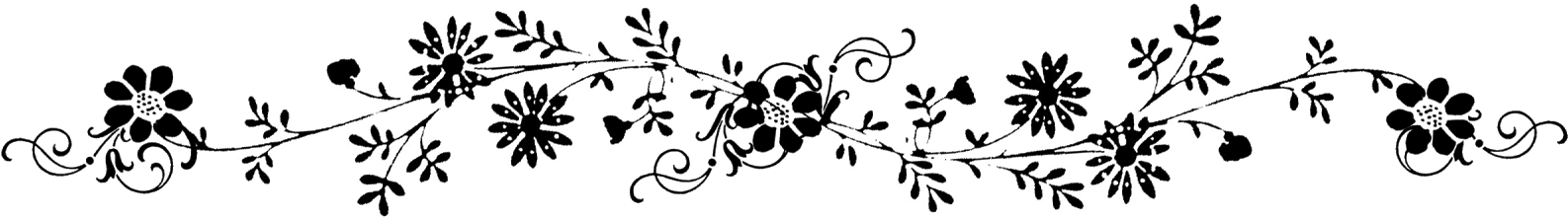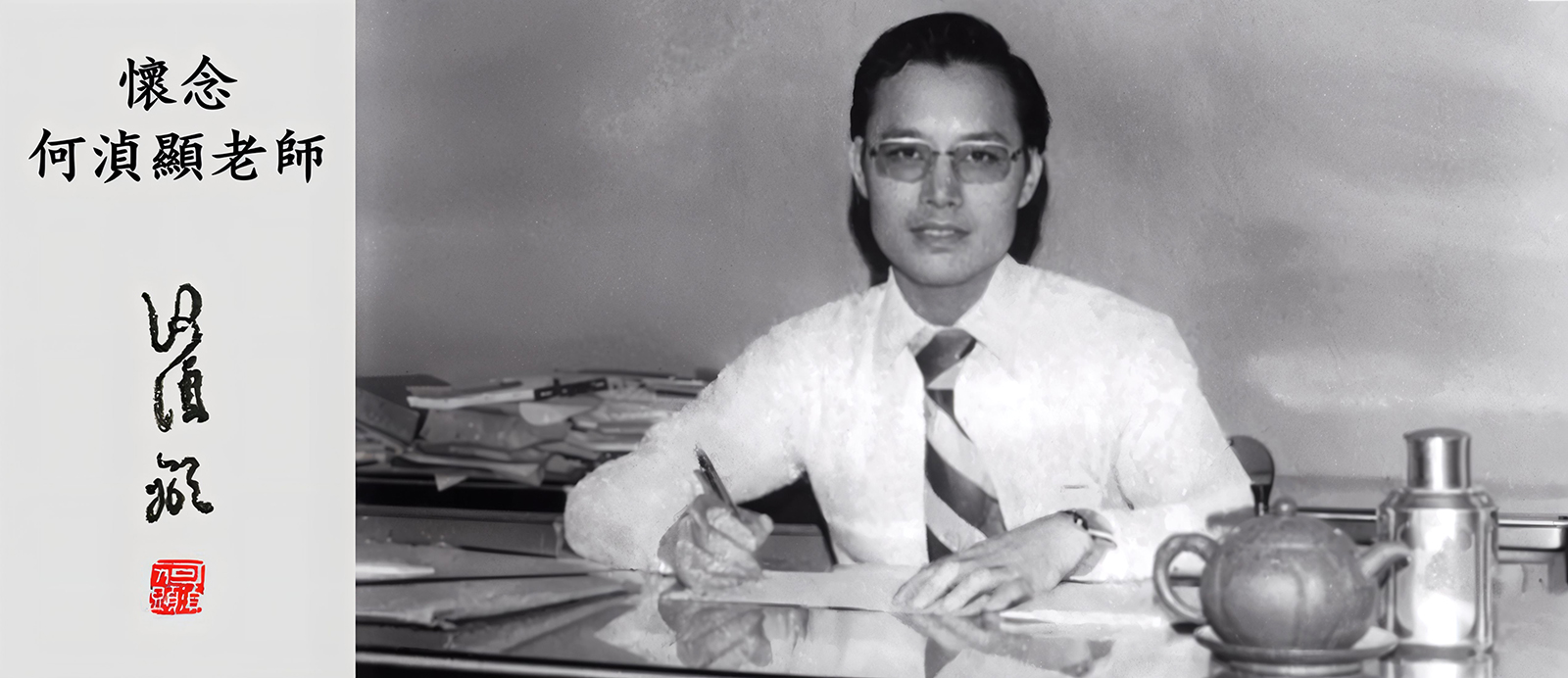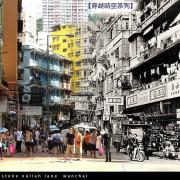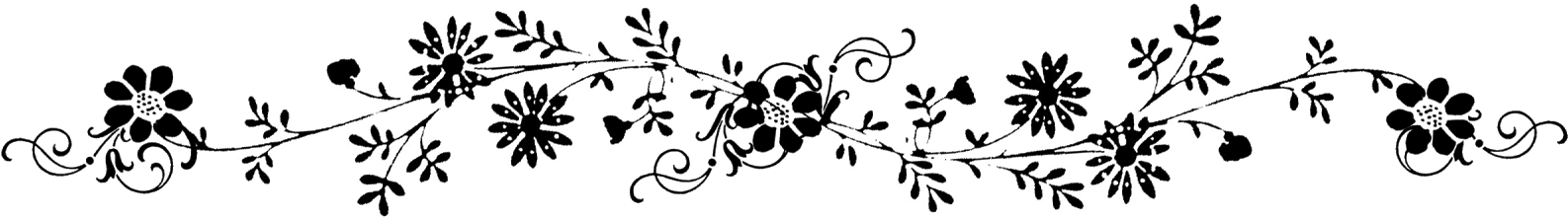
李潤滿
學生
2025-01-28
本文乃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2024年12月12至14日主辦「風雅傳承:第三屆民初以來舊體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古典詩詞創作比賽與推廣學習座談會」之創作體會分享,文中後半述及與何師啟蒙之恩:
月前喜獲第三十四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第十七屆填詞)公開組季軍,頒獎禮後荷蒙評判陳煒舜教授相邀作分享,實在深感榮幸。
是次填詞創作比賽的指定詞牌是《卜算子》,不限韻。剛好我近年喜步古人名章韻練習填詞,且在比賽徵稿期間與大學同窗於古琴雅集重逢,得聆故人及其琴社上下諸君腕底妙音,遂有感而步蘇軾、王觀及陸游三位古人的名作韻而成篇,一則倚聲以抒懷抱,二則投稿以試身手,僥倖蒙評判賞識,得以重拾逾三十年前在第二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第一屆填詞)學生組初次忝得獎項的喜悅,堪歎其幸何如!
我這次的得獎作品是一組三聯章中的首章。三詞全璧如下:
其一步蘇軾缺月掛疏桐韻
萬壑起松濤,一遣囂塵靜。流水高山意若何,香暗斜橫影。 新雨滴簷頭,故夢誰同省。滿袖風來側耳聽,不道單衣冷。
其二步王觀水是眼波橫韻
莫是淚凝成,一任風吹聚。雪裏依稀你我他,各有魂銷處。 若個喚之來,不忍揮之去。腕底春陽待放晴,卻按清弦住。
其三步陸游驛外斷橋邊韻
揮手撥朱弦,巧作群芳主。一似輕風拂檻來,播弄晴和雨。 俯首勸東君,莫把朝顏妒。只恐三春欲挽難,轉眼新成故。
此三詞寫瀞和琴社正副社長以及一位社員的演奏。若按雅集中的出場序,先是芳華正茂卻已轉益多師的社員邱爽女史、再是我在香港大學中文系的同窗故友副社長張為群博士,最後是壓軸的古琴泰斗社長姚公白先生。雅集在春日黃昏舉行,當晚我和闊別多年的張博士匆匆一面後即便揮別,夜裏文思如潮,半躺床上用手機上網查找網上版的《唐宋詞格律》以及三人所奏的樂曲資料,選好分以蘇軾「缺月掛疏桐」一首對應姚公白先生演奏的《烏夜啼》、王觀「水是眼波橫」一首對應張為群博士演奏的《長清》、陸游「驛外斷橋邊」一首對應邱爽女史演奏的《陽春曲》,近乎一揮而就,得詞三章,序如上述。
根據維基百科,《烏夜啼》古琴曲乃「以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之故事為題材所作,被收錄於約三十部琴譜中。首見於《神奇秘譜》,為中卷的〈霞外神品〉最後一曲。今有姚丙炎、吳文光依《神奇秘譜》打譜,以及管平湖照《自遠堂琴譜》打譜的版本」,當中所提及為古曲打今譜的姚丙炎,正是姚公白先生的父親。
姚氏乃浙派古琴世家,我幾年前因在書肆偶睹姚公白先生所整理的姚丙炎先生琴藝著作始知二人大名。我本俗人,不通音樂,唯其書裝幀甚美,忍不住當場翻閱摩挲之餘,更不禁上網搜索著者資料,其後大概社交平台根據我的搜索蹤跡推薦我往訪瀞和琴社專頁,才讓我有機會得逢琴社今年的春中雅集,再遇故人,並為斯事填詞抒感,繼而投稿參賽。
無論從即事成篇的緣起到查考詞譜,並在手機上編輯雲端文件和應名篇,現代資訊科技對今人創作古典詩詞的影響竟可有如此者,這是我當年初涉詩詞寫作時無法想像的事情!
然而變的是時代,不變的是人情。
回顧我的詩詞路,乃自九十年代初唸大學預科時棄理從文,因而受喇沙書院文學科恩師何禎顯老師啟蒙而始。何老師畢業於新亞書院,乃已故中文大學鄺健行教授的同屆同學。何師月前遽隨早一年仙遊的鄺教授返道山,積閏八十有三,福壽全歸。回想何老師當年任教我的時候,大概正在我目前這個年紀。在何老師的指導下,我參加了第二屆全港詩詞創作比賽(第一屆填詞)的學生組賽事,奪得優異獎的作品詞牌為《蝶戀花》,詞題「喇沙利道」:
七載黌宮沾化雨。徑對獅山,夾道亭亭樹。魚木花繁邀蝶侶。翠華如蓋堪消暑。 黃葉漫空秋共舞。歲盡枝零,美景憑誰賦。欲問履痕留幾許。未如今夕離情緒。
我習詩詞,由辨別平仄、揣摩格律以至琢磨立意、考究遣詞,一一皆由何師親授。其時恰好班中同學王明哲亦好文,每相砌磋,有時會互相鼓勵將習作交何師斧正,從中獲益良多。此篇為中學畢業的惜別之作,詞中的「魚木」乃遍植校舍正門外車道兩旁的喬木,每逢春夏之交即滿樹黃花,招蜂引蝶。近年社交平台常於花季泛濫賞花「打卡熱點」的帖文,假如當年有社交平台,大概我的作品在得獎後就會被我附上校舍前魚木花開的照片發成帖文,又或是「限時動態」了。然而當時的我雖往來喇沙利道校舍正門前的斜坡道七年之久,留下履痕無數,卻從未曾認真考究過道路兩旁一株株亭亭而立的大樹到底是哪一種樹,而若非何師給我批改初稿時賜示,我不知道我到底什麼時候才會知悉其名。
寫作,無論採用什麼形式,其中一項重大意義是用文字來梳理作者與世界的連繫,這是我在何師指導下學寫詩詞的過程中的一個小小領悟。何師逝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千古而下,凡我輩情之所鍾者,當同此慨。卅二年前的少作,需要何師點撥潤色才堪登大雅,卅二年後,我自步了這首少作的原韻以悼何師:
昔別朝陽今暮雨。宅外窗邊,依約從前樹。隔巷誰家曾共侶。書燈冷照幾寒暑。 擬效莊生歌且舞。流月溝聲,偏自吟愁賦。欲剪亂愁天不許。弦歌難復尋餘緒。
勞生悾憁,我和王明哲等當年文學班上的一眾同學自畢業後只於早歲拜訪過何師一回,聊表孺慕,其後各人半近失散,迨社交平台興起才輾轉重聚。八年前我曾代表同窗投書向何師問好,喜得何師親筆回函,信中提及我在信封上的回郵住址石水渠街竟正是何師年輕時曾寄寓之處。此悼詞上片寫的正是師生彼我間的今昔剪影,下片「流月溝聲」化用陳與義《臨江仙》「長溝流月去無聲」,寫的正是石水渠街的水溝。該溝在何師生活的年代尚是活水潺潺,到我遷至時則早已蓋成馬路,車塵漠漠。昔接何師來鴻,尚幸物非人是,如今則不獨物非,人亦非矣!
此二首《蝶戀花》分寫我和何師二人都曾留下不少足跡的兩條街道,既誌我與何師的師生之緣,亦是我個人橫跨卅二年參與全港詩詞創作比賽的一個小小紀念。